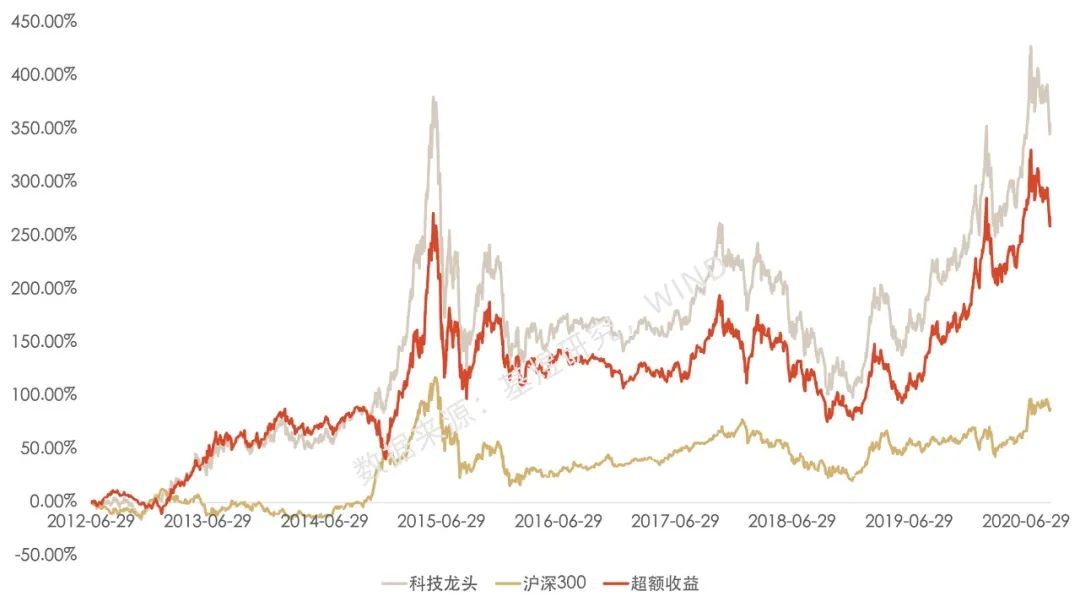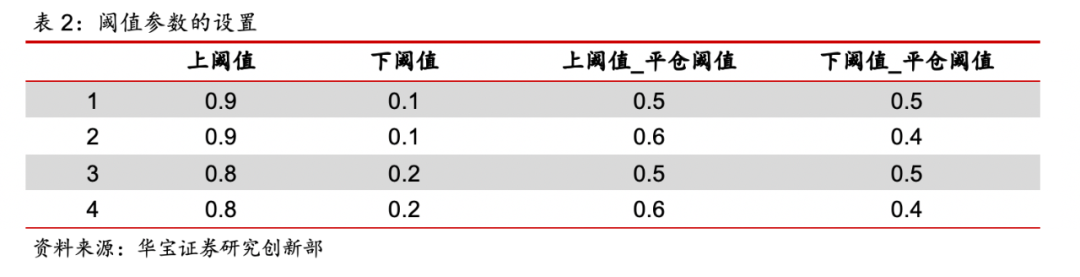在北京五年,我只住过朝北的房间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三明治 关注
原创 Zofonn 三明治
Zofonn在九月短故事学院里写下了关于“北面的房间”的故事。北漂五年,她搬过几次家,却从未住过朝南的房子。朝南,是家的温暖和庇护,朝北,则是工作后的独立与漂泊。通过小小的房间,她记录下作为一个北漂的真实心路历程。
文|Zofonn
编辑|二维酱
一百年前,伍尔夫说,女人要有一间自己的房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想告诉她,这间房最好朝南。
我也是最近才意识到房子朝向的重要。朋友说,尤其在北方,南北房间温差极大,租房还无所谓,买房千万别考虑朝北的,到时候想卖都不好出手。
当时我也没在意。可那天晚上,我把自己过去五年在北京住过的所有房子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发现它们竟然无一例外都是朝北的。
我心里突然有点不平衡,也开始问自己,我为什么从来没有住过朝南的房子?
答案似乎很明显,朝北的房子便宜。因为我总找那些房租便宜的房子,所以跟人合租的时候,我住的都是朝北的小次卧;好不容易一个人住了,一般的小户型开间也都朝北。
这当然也不是什么大事,只是对那天晚上的我来说是个不小的冲击。因为尤其是这一两年,我不断告诉自己,五年前我离开家来北京的决定是对的,我现在过得越来越好,做了喜欢的工作,赚了更多的钱……可是,为什么,为什么我明明觉得自己现在过得可好了,可我却从来没有住过一间朝南的房间?
我当然不是具体有多渴望一个朝南的房间。我更想表达的是,突然意识到自己这些年是不是过得并不好,我自我感觉那么良好,会不会是我给自己编织的一个假象?我为了要证明离开家是对的,所以不断给自己强化——你看,你看,我现在过得可好了。
而我再一想,发现自己从小到大睡过的朝南的房间,就是家里。
我家就在南方。这季乐夏第一轮达达演《南方》,彭坦开场一飙武汉话,我就绷不住了,泪直往外涌。我第一次听《南方》的时候还在大学,人在武汉,从没离开过家,也没什么特别的感触。这回一听,完全受不了。作为在北方呆了这么多年的南方人,在2020年这个夏天听《南方》,实在有太多感慨。
五年前,我在武汉混不下去了,工作没了,感情没了。我两眼一抹黑,拖了个行李箱,就来了北京。
第一份工作是坐办公室,朝九晚五,到点上下班,对房子的惟一需求就是离地铁近。我运气不错,租的前两个房子离地铁都不过五分钟,下雨没带伞也不怕。当时还是心气高,虽然挣的不多,也不觉得有什么,知道反正一切都是暂时的。卧室小点就小点,床够大就行;窗外正对着垃圾堆,没关系,窗台上放束花就是了。
我在一个不到七平米的小房间里住了整一年,那年我28岁。生日前,我下定决心要给自己换份工作。因为看见小区大门口贴了一张讣告,上面别的信息都没注意,就记住人家“享年56岁”。我一算,自己马上就过一半了,得赶紧做点真心喜欢的事。
半年后,我误打误撞成了一名记者。还是在那个不到七平米的小房间里,我连夜完成了人生的第一次采访,还写出了人生第一篇整版登报的文章。出刊那天,我一大早骑车去报亭买了五份报纸。我跟卖报的阿姨讲,今天这上面登了我的文章,阿姨笑了,让我指是哪篇。我打开报,专门指给她看,还特意强调,这中间两整版都是我写的。
那之后,每天的记忆就是写写写。伍尔夫说,一个女人想要写作,就要有一间自己的房间,我信了。2017年3月,我终于完成了这个宏愿,在北京的正北边住上了一间视野超好的高层小开间。虽然只有一年的使用权,但这对我来说足够了。我知道,至少在这一年里,它属于我,而且只属于我。
我完全沉浸在一个人拥有整间房子的喜悦之中,并不介意北边高层的风大,或是坐在飘窗瓷砖上会觉着凉。我在窗台铺上厚厚的毛绒毯,还在毯子上架起折叠的懒人沙发。天冷的时候,我不坐就是了,让我的灰龙猫、红狐狸、粉猴子们坐成一排,夕阳西下,阳光洒在它们脸上,也很美好。
为了彰显我是这房子的主人,我还打印了好多自己和家人的照片,用彩色小夹子把它们一张张错落地夹在白色的网格架上,挂在床头,做成照片墙。好多年前买的圣诞小彩灯也被我翻出来了,绕着架子边缘缠了一圈,天色暗下来后点亮它,好像看到一颗颗星星映在墙上。
可是,新鲜感似乎没有持续太久,我的生活就被一篇篇稿子淹没了,对那个房间的记忆也只剩下眼泪和鼻涕。
那年春天,我妈来北京看我。返程那天,我因为有稿子没弄完,也没心思送她去火车站,只是看她上了地铁就自己回了家。可能还是那会儿压力大,一到家我就一个人干嚎了一场,好像给自己演了一场戏。只不过,没哭几嗓子,我就停下了。当时心里很清楚,哭没有用,有那时间,还不如擦干眼泪,擤完鼻涕,一个字一个字老老实实把剩下的稿子写完。
印象中那年冬天特别冷。本来从地铁到家的路上,要穿过一条六七百米长的小道,但就在那个冬天,几乎一夜之间,路两侧的店全都搬走了,卖小商品的,卖水果的,卖干货的,还有平时支在路中间卖麻辣烫、烤冷面和煎饼果子的小摊。有的店门就那么敞着,屋里地上也只有碎玻璃碴。春夏那会儿,这里还好热闹。我妈第一次路过的时候,就被街边光着膀子满臂刺青的大哥惊着过,我也看过拌着凉菜的老板几句话不对付就放下饭盆出门跟人干仗了。可是,有一天,这里所有的烟火气,连同扩音器里循环往复播放的叫卖声,和师傅们因为错不开车愤愤按下喇叭而此起彼伏响起的哔哔声,说没就没了。
一年后,我不想再住在城外,没有安全感,就又搬回了城里,住进一个老社区。城里一居租金太高,我只能又住回朝北的次卧。北面窗外的树比站在五楼的我个头还高,叶子伏在窗前,伸手就能摸着。
其实,这个社区最吸引人的是楼下就有一排卖菜的,推着自行车打他们身边过,总能看到绿油油的小青菜和水灵灵的大萝卜。这些都是正规摊位,头顶有棚子,面前有石板,晚上收摊的时候,细心的老板还会用雨布和砖头把摊位盖好。我是真没想到,没过几个月,那一溜摊位竟然又没了,变成了一棵棵新栽的树。我甚至都不知道他们具体是哪天没的,因为我并不需要天天打那儿过,但当我后知后觉地发现我再也见不到他们的时候,心里还是很难受。
我又换工作了。一个从天而降的机会,正好记者写不动了,转去做编辑。半年后,我还是觉得合租不方便,大晚上洗完澡想吹个头发都怕影响别人,于是下定决心还是要自己住,就找到现在的这个房子。
这个房子我住了快两年了,是我在北京呆得最久的地方。在此之前,我几乎每年都搬一次家,可搬到这里,突然搬不动了。
当然,第一次见面,我就看上它了。三楼一开间,面朝小区里,立立整整,几乎没有浪费的面积。但我真正对它产生感情,还是要到2018年底爸妈来住过一个月以后。因为他们住过,让我觉得这个房子不一样了,像是开了光。
事实上,我第一天搬来的时候,妈妈几乎和我同时到。我是一大早跟着一辆金杯车装着行李,从城里往东开了四十来分钟,直接被拉到小区楼下;妈妈则是前一天从武汉上的火车,睡了一宿,再自己搭地铁,拉着她的小推车,找到我在五环外的家。
妈妈是想来帮我收拾屋子,但她刚来一周就病了。一开始我们都以为是肚子痛,后来挂了急诊,吊了两瓶水,还是不管用,医生才想到有可能是急性阑尾炎,需要做手术。当初打车找医院的时候,我怎么也想不到还有开刀这一出,就用手机地图搜了搜家附近的三甲,弹出来第一条就是它。车程显示二十分钟,我想成吧,打个针嘛,三甲总不至于太差。
谁想到这一路黄沙。车越开,周围越荒。我在车后排攥着我妈的手,没说话。初冬,大中午,天空浑浊,东边稍许透着红光。
我住的地方已经在五环外了,这条道明显通往更偏的地方。大路坑坑洼洼不说,最后还拐上一条小道,再开个三四百米,才看到一栋白色三层小楼,孤零零地杵在水泥地上。附近大概是刚拆迁完,房子都给推平了,就剩下这医院没动。路对面一个土包接一个土包,上面还罩着绿色的网兜。
说真的,还没进医院大门,我心里已经有点不是滋味儿了。要是在武汉,我们出门五分钟就能到市里最好的医院。如果不是我来北京,我妈为啥要跟我来这种地方受罪?
我爸也是因为我妈要开刀才专门来的北京。他前一天在电话里嚷嚷,不能开刀,保守治疗,我们没理他。结果,第二天早上,他五点从家出发,坐第一班高铁,十二点到北京西站,再折腾了快两小时才到的医院。他估计到了也很不适应,不是来大北京吗,怎么坐两小时车又把我拉到这么灰头土脸的地方?
好在手术很顺利。一周后,我们回了家,三口人在这个三十平米的小屋里挤了一个月。爸爸负责每天买菜做饭,妈妈后来好些了,又开始张罗着晒被子洗床单。
因为爸妈的缘故,我对这个房子平添了些眷恋。今年上半年疫情时,这里也让我感到安全。当时就觉得庆幸,首先是自己单独住,而且小区也不错,买菜供货什么的都安排得挺妥当。最难的时候,想象中所有不好的事情最后都没发生,让我又觉得好像跟这个房子一起经历了什么,像是一个战友,或者说是一个战壕,为我提供过庇护。
这其实就是一个方正的开间,也没有客厅和卧室之分,沙发和床自然区隔出了两部分。一进门,左手边是个大衣柜,右手边是个长餐桌。餐桌上现在被我铺满了,一边放着我干活儿用的电脑,一边放着我鼓捣脸的瓶瓶罐罐。桌上还放着一筒酒精湿巾,这是今年新添的。我进门洗完手摘完口罩就从筒里抽一张,先把我的钥匙擦一遍,再把门把手擦一遍,最近擦得倒是没那么勤了。
我都在沙发上吃饭,碗碟放在沙发前的茶几上。沙发是紫色的,有点笨重,靠背垫子拿掉可以变成一张床。我爸妈来的时候,我就睡沙发,这地方只能我睡,大小刚刚好。
我一般在沙发上看电视,尤其是今年上半年,说我长在沙发上都不过分。一到吃饭的时候,我就想打开电视,好像没有电视搭配,这饭就好像忘搁盐似的。从年初到现在,这个家除了我就没有别人来过。我就在这里,像一颗土豆一样,窝在沙发上,没有发霉,没有发芽,倒是长了个疙瘩。
片子上就是这么显示的,一节一节骨头都透着亮,就有一块黑色的暗影,不合时宜地卡在脊椎的曲线上,大夫说,这就是突出。我恍然大悟,原来我得的就是腰椎间盘突出。
我这个腰不是第一次疼了,但真要往回倒,好像也还就是这两年新添的毛病。这次犯病到现在三个月了,一直没完全好。最近的情况是,早上起来不行,身子硬的,右后方还是疼,但到了快中午就自动好了,好像身体活动开了,不知不觉疼痛感就消失了。
今年七月,我才第一次回武汉。错过了过年,错过了清明,错过了端午。回到家的时候,发现好像什么都没有变。该吃吃,该喝喝,跟之前的日子无缝对接。大家好像都默契地忘了过去的几个月。
坐火车回去的路上,我还很谨慎,心中感慨万千,觉得为了回趟家可太不容易了。结果回到家,发现自己的戏好像有点过。一切还是原来的样子。人没有变,家没有变,就像那些过去日子留在我们心中的执念一样,隐而不发。
是,跟过去的自己比,我确实每一步都比过去好,每一份工作薪水都比上一份高,住的每个房子都比上一个贵。我老说,如果遇见五年前的自己,她要是知道我现在做的事情,一定会很羡慕。但我想告诉她,即便我实现了她五年前的全部梦想,今天的我仍然觉得很挫败,觉得自己的世界随时会崩塌。
疫情是,腰也是。我就觉得我撑不住,它随时会折,即便我意识到我的身子是歪的,我也无法自我调整,它不受我的控制,这种失控感让人很绝望。
所以我才会有这么大的反应吧,为了一个朝南的房间。就好像这个事儿给了我一个信号,告诉我说,你醒醒吧,你看你,即便往前走了这么多步,可你还是活得很糟糕,要不怎么会连一个朝南的房间都没住上?
挫败感。对,这种挫败感,好像当年我已经在我能力范围内盛装出席了一场聚会,但仍然觉得自己是最黯淡的那一个。我就觉得我望尘莫及,不是不想追,可我真的已经在家捯饬了好久,觉得自己今天可以扬眉吐气了,然后一到那个场子,发现周围所有人都在发光,而自己的衣服好像廉价朴素到不值得出现在他们身边一样。从那之后,我就彻底不爱打扮了。
有时候,为了回避这种挫败感,即便知道眼前是一个泡泡,我也想待在里面,不愿意戳破它。当年,我可能只花了一个下午去打扮去赴一场约,结果发现自己是最黯淡的那一个;现在,我花了五年时间,离开家,离开南方,结果一个朝南的房间让我发现自己到头来还是什么都不是。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这五年,我觉得,我在跟自己和解,对那些莫名其妙愤愤不平的事同自己和解。我一直跟人说,我特别害怕冲突,也不会表达愤怒这种情绪,只会远离。但我突然意识到,我会对自己愤怒,我所有的愤怒都指向了自己。因为永远离开不了自己,我只能和自己和解。
就像这个朝南的房间一样,其实也是在跟自己置气,至于为什么,我也不知道。
作者后记
本来想在生日前在三明治把过去五年间的过往写下来作为礼物送给自己,可越写下去越觉得艰难。一开始确定主题的时候很兴奋,但到了搜集素材的环节就开始犯难。记忆太杂太散,又好像找不到一条清晰的故事线,能把所有散珠串起来。坦白讲,最后呈现出来的和我想象中“北面的房间”这个题目所能承载的还有一定距离,但这就是我当下能交出来的答卷了。谢谢二维酱,是她让我知道一个好编辑对作者有多么重要。
原标题:《在北京五年,我只住过朝北的房间|三明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