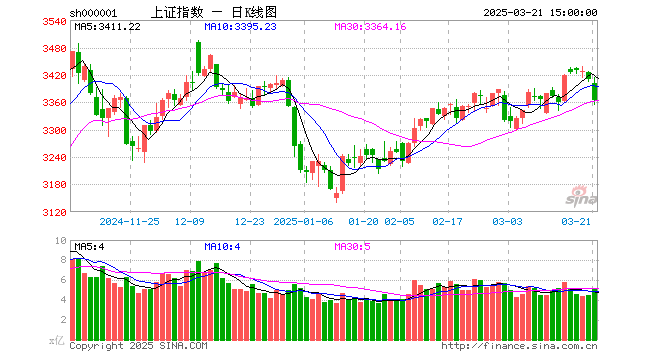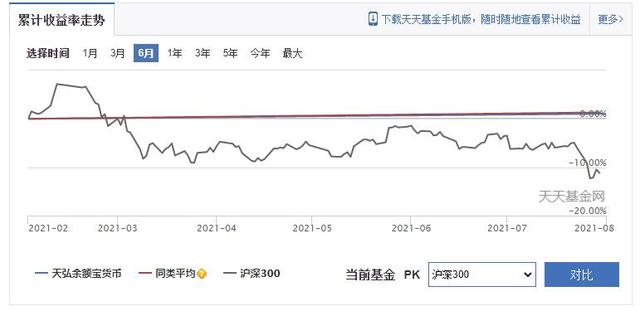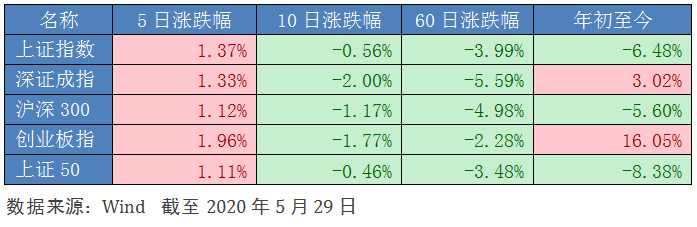近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深化医疗服务价格改革试点方案》。这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上任以来首次部署医疗服务价格改革,也是国家医保局成立以来覆盖地域最广、患者最多、协调利益最复杂的一场改革。长期以来,医疗服务价格改革是整个中国医改最难触碰的烫手山芋,它不仅像药品耗材带量采购那样涉及患者、医生、医药产业的切身利益,而且牵涉民生事业的兜底保障。2015年,由于遭遇当地民意激烈反对,重庆市原卫计委、原物价局不得不暂缓医疗服务项目价格调整。
价格与供求相互影响。为避免政府定价可能引发廉政风险、社会稳定风险、价格信号失灵风险,部分医改“市场派”人士主张尊重医疗机构自主定价,政府退回到价格规范制定者、价格透明度监督者的角色,不直接出台医疗服务指导价(或价格区间),在多元竞争格局下自动撮合出最优价格。
然而,不同于完全竞争市场,医疗服务的特性导致价格—供求关系出现失灵。一方面,医疗服务因鲜明的地域性(如:15分钟便捷诊疗圈)、很高准入门槛(如:医疗机构设置审批)而在客观上导致供给主体有限,极难通过价格的动态变化而灵活伸缩供给能力;另一方面,覆盖全民的基础医疗服务是居民的刚需,即便其价格(大幅)上涨,也无法调控社会需求减少,只会(大幅)增加刚需就医者的负担。纵观中国医改选择对标的部分发达国家,无论是公办医疗体制(如英国)、社会保险体制(如德国),医疗服务价格都或多或少处于政府管制状态下。因此,政府管理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成为我国医疗服务价格改革的主导模式。
医疗服务虽然常被要求产业性让位于公益性,但其他政府干预价格的行业有很大区别。医疗服务既不像水、电、煤气等自然垄断行业提供(半)标准品,服务类别数不胜数、服务链条长之又长;医疗服务也不像国防、公共道路等纯公共产品具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可以无偿向全民提供,而是实质上处于“半市场化”状态:公立医疗成为需要自筹运营资金的市场主体,其逐利动机并未被根除;与医疗服务产生联动的医药市场,也被分为被价格管制的医保市场、完全放开价格限制的非医保市场——这给政府直接定价带来巨大挑战。
在这一情况下,政府若基于“成本定价法”,往往价格一算出来,上游成本又变化了,当前价格就失去了科学性;若基于“产出定价法”,要想测算、核定医疗服务的产出,本身所耗费的行政成本、医疗管理成本甚巨。更尴尬的是,当价格改革被地方政府赋予鼓励医疗专科建设、鼓励创新产品应用、与当地物价水平(CPI)同步的施政目标,定价标准五花八门,也不太稳定,医生、患者对此无所适从。
对此,本轮医疗服务价格改革没有“一刀切”走“市场化”或“行政化”的道路,而是采取分层定价的策略:一方面对普遍开展的通用项目,政府要把价格基准管住管好;另一方面对于技术难度大的复杂项目,政府要发挥好作用,尊重医院和医生的专业性意见建议,更好体现技术劳务价值。
此外,本轮改革采取先试点、后推广的稳妥推进模式,这意味着决策层意识到确定价格均衡点的复杂性,希望提供一定的试错与容错空间。这是因为,过高定价可能激励医疗机构为扩大收入而实施过度医疗,过低定价也不一定会出现医疗不足——由于医生、患者之间存在明显的信息不对称、权利不对称、话语权不对称,在单价下降的情况下,医疗供给侧仍可能通过增加服务量以保持既定收入,这同样导致过度医疗的发生。
近几年,通过取消药品加成、药耗带量集采为患者降低了用药负担,为调整医疗服务价格创造了条件。通过“腾笼换鸟”,医疗服务价格早日调整到(接近)均衡水平,有利于缩短“降药价”与“涨医价”之间的时间窗口,形成对公立医疗机构的合理补偿机制,避免出现医疗技术水平下降、优质医疗人才流失等问题。
医疗服务价格改革绝不等同于看病涨价。本轮改革强调“总量范围内突出重点、有升有降”。但笔者还是要呼吁,需关注部分项目价格上调的民生影响。当前,我国医疗服务有三大支付方:公共财政(约占15%以内)、个人自付(约占30%以内),基本医保(约占60%左右)。基本医保已经成为我国公立医疗体系的最大支付方,应当发挥对患者“封顶保障”的能力。具体而言,通过强化价格监测评估,明确调价的启动条件和约束条件,对基本医疗服务不得不上调价格的情况,建议基本医保资金予以专项保障,确保患者实际就医负担不明显增加,不因医疗可负担性低而产生因病致贫、因贫弃疗等困境。
(文章来源:经济观察网)